李鸿章西游记
1896年,一股中国旋风席卷欧美。
旋风来自一位年逾古稀的中国老人。这位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带着自己的棺材,历时190天(3月18日-10月3日),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等8个国家,横跨三大洋,行程9万多里。所到之处,受到上至王公大臣、下到黎民百姓的热烈欢迎,万人空巷。
他那超过1.8米的高大身躯,以及雍容的气质、坦率的谈吐,令西方朝野为之倾倒。从此,脑后拖着“猪尾巴”(Pigtail)的中国人,在欧美报刊的漫画中,不再只是丑陋粗鄙的代表;中国人第一次以健康、正面的形象,出现在不少欧美产品的广告中,连《纽约新闻报》(New York Journal)这样的大报,也将这位老人阅读该报的漫画,作为报社的形象广告。
这位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人新形象的老人,他的名字就叫做李鸿章。
李鸿章出访欧美之前,正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在远东有切身利益的俄国,联络德国和法国,出面逼迫日本归还辽东。俄国迅速被中国朝野视为可靠的“老大哥”,中俄亲善俨然已经成为“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了。
甲午战争正酣之际,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病逝,其子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即后来被列宁下令处决的末代沙皇)即位。中国派遣了正在京述职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以头品顶戴作为唁贺专使被派出使俄罗斯。
王之春与老毛子结缘,在他署理广东布政使任内。当时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二世来访,广东巡抚刘瑞芬因病(不知是否装病)回避,王之春代为接待。这位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七世孙,在湘军崛起时,以弱冠之年投笔从戎,后专注于外交,著有《谈瀛录》、《清朝柔远记》等书,俨然洋务人才。
登基后的尼古拉二世确定将于1896年5月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于1895年12月28日决定再派王之春出席。但俄国公使喀西尼(Aruthur P. Cassini)立即提出,王之春品级太低,希望该派宗室王公或大学士出使俄国。
1月4日,光绪皇帝与翁同龢商量出使人选。御史胡孚辰被选定给朝廷找个台阶,他上奏称王之春资望太轻,似宜派李鸿章前往。2月10日,已经是腊月廿七,朝廷以慈禧太后懿旨的名义,宣布改派李鸿章为正使,邵友濂为副使。
春节一过,2月14日(正月初二),李鸿章上《吁辞使俄折》,一方面称“现在中外大臣,通知洋情,娴习仪节,堪膺专对者,尚不乏人”;另一方面则乞怜说:“微臣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有余之海路,时逾数月,地隔三洲。凡风涛寒暑之交侵,实疾病颠连之莫保…… 即使凭杖威灵,长途无恙,亦岂能以残躯暮齿,从事于樽俎之间。倘陨越于礼仪,殊有伤于国体”。因此,他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别简贤员。”
第二天,圣旨下:“李鸿章耆年远涉,本深眷念,惟赴俄致贺,应派威望重臣,方能胜任。该大学士仰当体仰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驰驱,以副委任,无得固辞”。
如此严命,李鸿章只好领旨,便上了一份《使俄谢恩折》表态说:“俄国本通聘最早之邦,而加冕又异俗至崇之礼,但有益于交邻之道,何敢惮乎越国之行?”
同日,朝廷命张荫桓接替李鸿章与日本谈判通商条约的事宜,李鸿章总算甩开了又一个“奉旨卖国”的苦差。
2月20日,光绪皇帝再次下旨,命李鸿章同时访问德法英美等国。次日,还加恩给李鸿章儿子李经述赏带三品衔,随同出访,以便照顾李鸿章生活起居。随后,又根据总理衙门的奏请,命李鸿章与出访各国商量提高关税的事宜,为支付给日本的巨额战争赔款开源。
李鸿章立即开始出访准备。在他2月25日上奏的《随带人员折》,附了两道片奏,一是《洋员参赞片》,请皇帝批准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所奏,带外籍税务司柯乐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维德(美)等五人随行。
另一道片奏则是《李经方随往片》,从这份附片很能体察李鸿章当时的心境。当时,朝中有人攻击他带长子李经方随行,他对此进行了反驳。李鸿章说,李经述向未学习洋务,此次随同出访只能“在起居动履方面尽心侍奉”,而李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于各国风土、人物、往来、道里,均所熟谙……若得李经方同行,则程途之照料,宾客之酬应,均可分劳。”
李鸿章坦率地道出了心结:“马关之役,势处万难,所有办理各事,皆臣相机酌夺,请旨遵行,实非李经方所能为力,局外不察,横腾谤议,应邀圣明洞鉴。”朝廷将“卖国”的使命尽交李家父子,这是李鸿章最耿耿于怀的,而上年甚至还指定李经方负责向日本交割台湾,李鸿章极力推辞,遭到光绪皇帝痛斥。李鸿章力争李经方随行,很有些分谤的考虑在内。
2月28日,正月十六,花灯正闹的时节,慈禧太后接见了李鸿章,密谈数小时。一般认为,他们谈的焦点就是与俄结盟的重大外交战略。
联俄之外,李鸿章此次出访还有一个使命:提高关税。在列强武力压迫下,当时的中国关税仅为“值百抽五”(即5%),几乎成为自由港,但对日巨额赔款,却不得不再打关税主意。这又是一桩不容易见效的苦差使。
不少野史、乃至一些职业历史学者,还有种说法认为派遣李鸿章出访是因为慈禧太后“酬庸”。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那个年代,将万里奔波的苦差使作为酬劳,交给一位七旬老翁,这样的逻辑我实在难以理解,估计这是将今人对出国的向往之情套在了古人们身上。
而在促成李鸿章出访的各种因素中,各方研究者恰恰忽略了最为关键的一点:“黄祸”(Yellow Peril)。
甲午战争后,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黄祸论,担心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 “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克纳科弗斯(Knackfuss)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 Yellow Peril)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黄祸图》的画面上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天使手执闪光宝剑,正告诫着欧洲列强的各保护神:“黄祸”已经降临!悬崖对面,象征“黄祸”的佛祖(指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正向欧洲逼近。天空乌云密布,城市在燃烧,一场浩劫正在发生。威廉二世还在画上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在这样的人种危机感中,在停战后的中日之间进行分化瓦解,是一种很正常的心态。根据美国《芝加哥先驱报》(Chicago Tribune) 1896年6月21日报道,德国媒体和民众对李鸿章的访问表现了热烈的兴趣,而同时访德的日本名将、著名政治家山县友朋,却受到了冷遇。虽然德国在野党认为这是大错误,但德国政府照样“亲华反日”。在这些背后,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合纵连横”的影子。正如李鸿章本人在《使俄谢恩折》所说:“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实交际所宜隆。”
1896年3月14日,李鸿章到达上海,在这里进行出国前的最后休整。
日本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说,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后,“寻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各国的报纸报道说,李鸿章为这次出访带了一口华丽的棺材,以免万一客死他乡。尽管《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随后采访李鸿章的发言人时,证明“这是一个编造的故事”(1896年8月29日),但在四年后,《纽约时报》却再度报道说李鸿章出访时所带的棺材将在法国马赛进行拍卖(1900年6月10日)。
至于李鸿章是否真的携带了棺材出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老大帝国的外交关系与国际运筹,不得不依靠一个随时可能谢世的七旬老翁去远涉重洋,这棺材、或者说棺材话题本身,就预示着大清的命运?
中俄结盟:一场苟且的闪婚
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到达俄罗斯旧都莫斯科。根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参与沙皇加冕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李鸿章所受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而李鸿章几乎是嘉宾中唯一的非皇室成员。
当然,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绝不只是对一个“大政治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也绝不只是展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而是有着更为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中国太需要朋友了。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鸿藻之孙李宗侗(玄伯)就认为,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就是俄国。李鸿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欧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天朝帝国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主动地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了。
国际的反响是热烈的,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Sergei Yulyevich Witte)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Esper Esperovich Ukhtomsky)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其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俄,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只有沙皇、李鸿章及担任翻译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三人。俄方强调其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在与沙皇的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倒是李鸿章本人因为对日和谈后成众矢之的,默不敢言。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龢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龢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龢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均由翁同龢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另一个政界大佬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角,法国依仗教会诱拐中国百姓(当时法国正担任天主教护教国),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并不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当时奉行门罗主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张之洞认为,从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还是件双赢的好事,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愈加感觉俄国够哥们。中俄密约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就迅速地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这在凡事推诿、拖沓冗长的大清来说,的确创造了一种“莫斯科速度”。而在北京举行的换约仪式中, 翁同龢等要臣均出席,并在签字后“举酒互祝” ,互赠礼品。吊诡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早请示、晚汇报,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却依然将这笔“卖国”的帐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了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了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了三百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在其于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说,俄财政大臣维特为感谢李鸿章推动建筑铁路一事,将付给李三百万卢布。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后出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在其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中,也提到了的确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
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最大的特别经费,虽然名为“李鸿章基金”,但经众多历史学家考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帐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三、这笔基金的确有一百七十万卢布被中国人领取(有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官方从合资铁路公司中获得的津贴);四、该笔基金更多地是被沙皇本人当作了小金库,支出浩大。
维特本人对次是否认的,但国内有历史研究者认为这是他在为李鸿章掩饰。其实,细读维特回忆录,他还提到当1897年俄国因侵占关东地区而与中国关系紧张时,他曾提议给李鸿章赠送五十万卢布,维特说这是他和华人交涉中唯一的一次贿赂,而且李鸿章是否收下该款尚不得知。可以肯定的是,维特并没有为李鸿章作尊者讳,他对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中收受贿赂的否定,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超规格的接待、加冕典礼的极尽奢华以及中俄密约的顺利签订,这些都令李鸿章在俄罗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中俄密约墨迹未干,“同志加兄弟”的老毛子便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与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
史家一般认为,在中俄密约一事上,中国被暗算了,黄遵宪在挽李鸿章的诗中就有“老来失计亲豺虎, 却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叹。但次类事后诸葛亮的见解并无助于厘清历史的真相。
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未必是权宜伎俩。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在甲午战争“伐交”层面上,日本正是在英日条约修订后的次日,才敢下达向中国开战的总命令。而英国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止俄国。作为反制,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英国报刊上就有评论认为,认为李鸿章被俄国人的甜言蜜语所骗的想法是幼稚的,中俄结盟完全是有利双边的选择,新经重创的中国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维特则认为,俄国执政者后来的短视,破坏了中俄密约的战略意图。他直率地指出,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侵夺行动,实为反条约,达到极点”。他担心如此背信弃义,将刚赢得的中国对俄好感一扫而空,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为此,他与军方进行了激辩,甚至要求俄军立即从旅顺大连撤军,用实际行动赢回中国人的谅解。
维特的担心成了事实,俄军的铁蹄令中国人、尤其是李鸿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卖、被愚弄的痛苦和愤怒。经此创痛后,中国的外交再度由“有联有拒”往回收缩,但不只是退回到“一体拒外”,而是“一体仇外”,终于爆发了玉石俱焚的义和团运动。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尽管清政府宣布中立,但无论朝野,都一边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边,不少中国人甚至与日军并肩作战,而孙中山、秋瑾等人,也一次次地为日军的胜利而欢呼雀跃、大唱颂歌……
一段以海誓山盟开始的浪漫情感,本可以发展成相濡以沫的模范婚姻,却在野心者的短视中成为了苟且的偷情。中俄之间从此注定了挣扎在互不信赖却不得不时时勾肩搭背的孽缘之中。而对于1896年正沉浸在加冕盛会狂欢中的李鸿章而言,他所能做的的确只有为自己“以夷制夷”的再度成功而自豪,并终于有了足够良好的心情,去会见那等候在下一站的伟大的俾思麦……
李鸿章令德国歇斯底里
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开始了德国之行。从他进入德国国境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比俄国更为隆重的礼遇,规格之高,俨然国家元首:
他下榻于著名的恺撒宫(旧译“该撒好司”),“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 莫不投其所好”,甚至连他喜欢抽的雪茄和喜欢听的画眉鸟都事先安排妥当,寝室内高悬他本人及“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照片,以示敬重;
他在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其皇后递交国书后,德皇夫妇还专门摆设国宴,隆重宴请中国代表团,并亲自陪同李鸿章观看军事操演;
德国首相、外交大臣等轮流着宴请代表团……
凡此种种,都远远超越了接待一国特使的应有规格。同期到访的日本名将、著名政治家山县有朋,就没能享受到这些高规格的接待,山县在接受记者询问时,只有自嘲说“中国毕竟是大国嘛”。
德国各报不惜篇幅地描绘了中国“副王”的各项行程。英、法等国报纸,则带着复杂的情绪,在对德国人的逾格接待予以了嘲讽。著名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认为接待李鸿章的规格本应恰如其分,俄、德两国将李鸿章或奉为帝王,或奉为三军统帅,“贡谀献媚”,如此逾格,反而容易令中国人对两国产生蔑视心理。该报指出,英国接待李鸿章固然应该热情,但李鸿章作为“英国人民的朋友”,绝不是为了英国利益,而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英国对此不需要感谢。
英国报纸的基本论调是,德国人为了拿到中国的大笔军火定单,对李鸿章过于奴颜媚骨,而当李鸿章离开时,并未采购任何军火,这令德国人失望至极,进而转为满腔怨愤。
其实,觊觎着李鸿章大笔军火定单的,自然不只是德国人而已,包括英国在内,都莫不竭尽全力向这位中国政治家推销自己的军火。
德国人的问题,在于其“吃相”的确有点难看,不像老牌帝国那样善加伪装。在英国人看来,刚刚崛起的德国人实在有点暴发户的轻浮,而在世故的李鸿章面前大失脸面。
当甲午战争爆发后,英俄等国为着如何在中日之间合纵连横而煞费苦心,德国人却无事一身轻,向中日两国大肆推销军火。当时的德国外长罗敦干男爵,在外交晚宴上就赤裸裸地表示,“欧洲国家能从东方人相互间的战争里获得的唯一利益,就是向他们出售军火。”战争期间,日本和中国的采购团,在柏林频繁出没,这与英国因宣布中立而向中日两国禁售武器形成鲜明的对比,令英国军火商们羡慕不已。德国舆论则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东方普鲁士”日本,不仅认为这是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的战争,更是一个新兴国家对一个老大帝国的挑战。战后,日本政府还将甲午战争期间所收到的德国民众声援信,结集出版了《在对清战争中德国人对日本的祝贺》(Deutsche Gluchwunsche an das siegreiche Japan im Kriege gegen China)一书,以日、德文字发行。
但在战后,德国人却一反常态,对中国备加呵护,与法国一道,积极参与了俄国牵头的对日压制活动,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一举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干涉还辽的三国,自然都期待着中国的回报。
但李鸿章的出访,并没有带着采购军火的使命,不仅德国的军火商们失望,就是对德国备加嘲讽的英国军火商们,也大失所望。更令所有西方人大跌眼镜的是,李鸿章的此次出访,并不如他们预期地那样恢复了甲午战争后被贬的政治地位,相反,以七旬高龄远涉重洋回到国内后,李鸿章反而进一步受到政治打击,最后被支到了远离北京的广州看守大清的南大门,彻底远离政治中枢。中国的政治风气则进一步转向保守,西方商人们的所有期望,最后被义和团的血红大旗彻底毁灭。
德国人毕竟不如老牌帝国的英国人那么深沉。李鸿章出访后的第二年(1897),中国政府任命黄遵宪、罗丰禄和伍廷芳分别出使德、英、法,只有德国政府坚决拒绝黄遵宪,而黄遵宪本人与德国并无任何过节,国际外交界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英国报纸认为:正是因为德国政府后悔接待李鸿章时礼节过于隆重,担心因此反而被中国人小看,便借机拒绝中国使节,以便“自增其威”。
到了1898年,德国人更是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事件,出动大军,强占胶州湾。梁启超认为,这是德国人为了报复“面子”被扫而进行的报复。其时,干涉还辽的三国中,俄国早已在北方得到了好处,法国也在南方得到了势力范围,只有德国,在向清廷索取福建的金门岛时,被“峻拒不许”。梁启超认为,胶州事件中,“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
又过了两年(1900),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也为了“德意志的尊严”,不听劝阻,非要在遍地义和团的混乱北京,只身前往总理衙门会谈,路上因与清军发生争执而被杀,引爆了义和团与驻京外交机构之间的血腥冲突。倍感丢脸的德国,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威廉二世在为这支军队送行的时候,要求他们对中国人必须残酷无情,“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小窥德国人”。
德国大军是八国联军中最后一支到达的,他们到达时,联军已经占领了天津和北京,大的军事行动已经完结,但德军依然对京津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屠杀,并纵兵捣毁了中国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在与李鸿章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德国专门约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派出亲王规格的高级代表团,前往柏林道歉。继李鸿章访德之后的第二个中国高级代表团,由末代皇帝溥仪的老爸、醇亲王载沣率领,区区数年,中国代表团由上宾沦为末客,德意志的天似乎有点阴晴不定。至于此后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德国尽管与日本是盟国,却对中国给予了很大的同情,这些正是中德历史深处的吊诡所在。
在李鸿章的德国行程中,最引起当时的记者和后人们兴趣的,就是他拜访俾斯麦。在场的各国记者进行了详细记录,无不大同小异。有意思的是,在曾经轰动英美的《李鸿章回忆录》中,记载了俾斯麦告诉“东方俾斯麦”李鸿章说,法国人可并不将“俾斯麦”一词视为任何恭维语,而且自己也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这段对话,十分传神,但《李鸿章回忆录》已确证系由美国记者曼尼克思伪造,因恐其或许引述自当时报道,我还遍查各国报纸,都难以找到其出处,估计很有可能是曼尼克思的个人创作。
俾斯麦这句真假难考的谦语,却真正道出了其与李鸿章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人。梁启超认为李鸿章难以与俾斯麦媲美,“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任公的这一定论,实在是对李鸿章不公之至。中国政坛风波险恶,远非一个朝气蓬勃的德国所能想象,果真易地以居,在曾国藩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的中国政坛,以俾斯麦的强势,一定会落个“野心家”加“阴谋家”的悲惨结局!
当李鸿章与俾斯麦执手言欢、惺惺相惜时,他是否在内心深处向往着那种痛快淋漓的政治与人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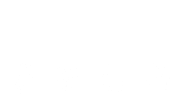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