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房改是当下的民生 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新京报:医改、房改关系当下的民生,关乎健康和生命,无疑十分重要;但是,教育体制改革关乎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和命运,关乎国家兴衰、民族未来,它是不是至少也具有与医改、房改同样的重要性,甚至更为重要呢?
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卫生部透露国家已经制定了6个不同的卫生体制改革方案。据介绍,国务院成立了有15个部门参与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部级协调工作小组,平行委托国内著名高校、国务院研究机构、国际组织以及著名国际私人机构等6个机构分别制定方案。
这一消息意义重大,不仅表明我国医改已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意味着对改革模式的改革有重大突破。委托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专业机构、非政府组织参与制度改革的设计,打破了以往主要由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方案、自己改自己的陈旧模式,是我国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上迈出的一大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与此同时,我感到的是教育的失落。医疗卫生、教育和房地产等领域虽然都迫切需要改革,但它们的改革位势却完全不同。房改早已激烈如战场,争论此起彼伏,不知有多少对策和方案。医改从对宿迁改革的争议而启动,至今也已经有了6个方案。然而,我们的教改方案有几个?
医改、房改关系当下的民生,关乎健康和生命,无疑十分重要;但是,教育体制改革关乎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和命运,关乎国家兴衰、民族未来,它是不是至少也具有与医改、房改同样的重要性,甚至更为重要呢?教育的改革问题,至今尚未提到议事日程的事实,与我们至今未能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一样,再一次凸显了我国教育面临的严峻局面。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缺乏对教育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也许,应当拍摄另外一部《大国崛起》,认识知识权威的确立、教育的普及和改革与国家繁荣进步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进入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近20年来,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竞争异常激烈。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的著名研究报告《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就是这种危机感和国际竞争的生动写照。此后,美国每一年都会发表类似警示教育问题、呼吁教育改革的调查报告,每一届总统都会提出教育改革的纲领,以教育总统自诩。它揭示了发达国家首先是教育发达,落后国家首先是教育落后这一事实。
近年来,我国在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上取得很大成绩,改善教育的主要努力是在增加教育投入上,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应当看到教育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长期以来,教育的贫困掩盖了教育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无论中小学严重的应试教育、炽烈的择校热;还是高等教育的官本位、培养质量、学术腐败、发展模式等,都不是靠简单地增加投入可以解决的,而有赖于实质性的体制改革。由于教育品质、教育产品的质量具有复杂性、潜在性、迟效性等特点,不像经费短缺、乱收费那样明显和直接,对决策者不易形成明显的压力。同时,由于教育改革牵涉面广,影响面大,一旦改错了后果严重,迟迟不改倒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安全的决策。但这却是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如果我们满足于问题不大、水平尚可的自我安慰、自我麻痹,在实质性的教育改革上无所作为,那么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每一个家庭都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教育改革刻不容缓,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建议中央政府如同重视医改和房改那样重视教改,尽快将教育改革提到重要议事日程。由于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世界各国的教改都伴随广泛的公众参与,由政府、专业组织、民间团体等制定不同方案,并通过旷日持久的公开讨论以形成共识,避免犯错。我们不仅期待,也在行动,正在制定民间版的中国教育体制教改方案,以实际行动启动这一进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杨东平)
薛涌:在哈佛人看来,学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而不是成为一个什么专家,掌握什么具体的谋生技能,这也是大学和社会对学生的最大责任
哈佛的前校长萨默斯,从上任到离任一直不停地告诫哈佛不要自满自足,必须锐意改革,否则就要落伍。美国高等教育界也普遍有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感到目前大学的教程陈旧,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必须尽快改革。萨默斯在任上,把改革核心课程当成一项重大使命;但他很快卷入各种争议之中,最后被教授们逼下了台,核心课程的改革也不了了之。
然而,就在萨默斯下台后的三个月时间里,由六位教授和两位本科生联合起草的核心课程改革方案迅速出笼。而这一方案比起萨默斯任上提出的方案来,大胆得多,顿时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热点。这个方案最令人瞩目的,是使哈佛成为常青藤中惟一一个把宗教和美国史作为本科生必修课的学校。
具体而言,此改革有四大目标:一、培养全球性的公民;二、发展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三、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德面向;四、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品,又是创造这一传统的参与者。
这四大目标,以核心课程的方式显示出来。所谓核心课程,是所有本科生都必修的基础课,即通才教育的主干。哈佛把这些核心课程分为七大领域:文化传统与变迁、道德生活、美国、世界中的(各种)社会、理性与信仰、生命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所有本科生还必须修一门写作课并掌握一门外语。
与现有的核心课程相比,这一新核心课程给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知识领域,而淡化在某一具体题目上的深度。换句话说,就是求广不求深。这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大学要为学生面对现实生活作实际的准备,而不仅仅是提供专业知识。根据统计,哈佛只有4%的新生把当大学教授当做自己的事业目标;只有5%的毕业班学生准备读文理学院的博士。哈佛显然不是为培养学究而存在。
这个方案中最可注意的是两项:宗教与美国历史。方案的起草人,英国文学教授Louis Menand指出:“宗教将在这个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三四十年前我们预料不到的。”据统计,94%的哈佛新生讨论宗教问题,71%参与宗教仪式。于是,理性和信仰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学生必修的领域。学生无论是修“为什么美国人热爱上帝而欧洲人不热爱”,还是修“达尔文讨论班:近化论和宗教”,都能满足这一要求。同时,美国史也被大力强调。诚如Menand所说,时代不同,世界不一样了,但基本的理念并没有变。核心课程就是要向学生传授美国的基本价值。
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实行,还必须看11月教授会议上是否能被投票通过。在投票之前,通过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的可能性也相当大。不过,从这个方案,我们还是能够看出美国高等教育的几个动向,值得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注意。
第一,随着科技的发达,大学教育不是变得越来越专,而是越来越博。教育的核心不在于让学生掌握什么具体的深度知识,而是让他们具有适应变化的能力。
第二,向学生传授道德和价值观念,是教育的核心。在七大核心领域中,理性与信仰,道德生活都是直接讨论价值观念的。文化传统与变迁等领域,也与此相关。美国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社会都需要一种核心价值系统和道德规范作为粘合剂。
第三,我一向强调大学要尊文史。哈佛的教改方案也证明了这一点。核心的七大领域,只有两个是科学范围的,其他都可归于文史类。可见文史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在人家看来,学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而不是成为一个什么专家,掌握什么具体的谋生技能。这也是大学和社会对学生的最大责任。这种责任,必须通过文史类教育才能完成。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课程过于实用化。名校纷纷设立管理学院,吸引最好的学生,形同工匠作坊。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市场上走俏的专才,而不是未来社会的领袖。在大学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中,非道德化的倾向十分严重,甚至许多人干脆把道德看成是对人性的压抑,不懂得道德是个人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社会的基本责任。这样的教育,很难培养未来良好的公民。我们一天到晚喊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几乎没有人讨论大学的核心使命:基础课程的设置。现在,该是把我们的精力转移到具体的教学内容上来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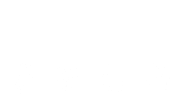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